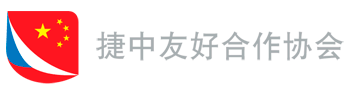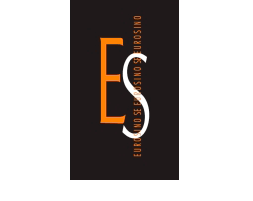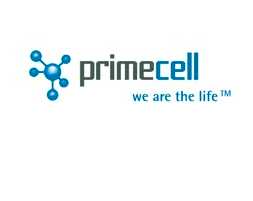捷克政府在几周前展开的与中国政治关系的恢复经过了扎奥拉莱克对北京的访问后终于有了具体的形式。
十四年以来,捷克外长首次与中国外长进行了会晤。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内阁其他几位成员也将访问中国;捷克总统计划秋天访华,同时总理的访华行程也正在准备中。
我们应该欢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开展的政治谈话和会晤。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今是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员;中国是我们在欧洲以外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近几年对中东欧地区的发展非常感兴趣。
中国所依靠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和我们西方的差别很大。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因此使得西方担忧,两边有过摩擦、误解,也有过纷争。但中国的不同也给我们竖立起一面镜子。通过中国我们才更了解我们自己 – 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优势和劣势。
通过跟中国的对话我们能更好地认知自己,超越误解,然后共同面对国际问题。只有当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真的具有国际性时,而不只是西方式的,才有可能在被世界所接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西方已经不再是绝对的领袖,而是重要力量之一,就像中国一样。这样一来,恢复捷中关系是绝对重要的,是不可被质疑的。
在这种背景下,捷克政府的对华政策依然受到了各种质疑。在这些质疑背后隐藏的大多是对世界的平视,或是无知。一方面,政府受到了经济实干家们的表扬,因为他们希望捷克企业登陆中国市场时会更简单,也希望因此能带来来自中国的投资。
另一方面,政府受到了坚持原则的卫道士们的抨击。他们批评政府忘记了西藏和人权。其实没有一方是完全正确的。
这两个“半真理”的简短结合促成了体现所谓捷克外交政策的漫画,图上画着为了肮脏的钱而卖掉了哈维尔的原则。最近,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卡雷尔•施瓦岑贝格也借用了这个漫画,将我们的外交政策比喻成卖春的放荡女子。
事实和这些说法其实相差得很远。政治关系的恢复的确是实现捷克经济利益的条件之一,但其本身并不能一定保证这些利益都会实现。因为中国的特殊条件,任何想要在中国市场上得到长期回报的外国人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而且中国在其内陆地区还有很多投资机遇,中国的对外投资目标也不完全符合捷克提供的条件。中国大量投资原料、农业用地、高新技术或战略基础建设等方面。捷中关系中尚未被利用的贸易机会肯定是有的,但是不能盲目高估它们。最终的实现还是要看捷克企业的能力。从这一方面来看,没有现成的钱是摆在桌子上等我们拿。
但捷克也不是要通过恢复政治对话卖什么东西,就更不用说要卖掉自己了。捷克希望将官方有关人权问题的对话继续下去,并在实用层面上给维权人士提供一些人道主义和道德上的支持。
我们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尊重广义的人权。而广义人权所代表的是比原来公民权范围更广更清晰的人权概念。
这使我们能看到中国近十几年来的巨大社会进步,看到这么多的政治注意力都集中在受到严重影响的生态环境上以及反腐败的决心。
现在的外交政策也映画出在西藏问题上更均衡的态度。这种外交政策感知着这个中国自治区因各种种族、文化和现代化发展所造成的复杂情况。它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各方之间展开包容性的对话,这也是世人期待中国领导人会做的事。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西方不能通过外力强行让中国展开这种对话。
在这里也需要对哈维尔时期开始的传统说两句。1990年,哈维尔在布拉格会见了西藏达赖喇嘛。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着个人和时代意义的独一举动,是两位长期被共产党政权监视的公众精神领袖的会见。在那个年代的气氛里,哈维尔完全可以不去思考这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
特别是达赖喇嘛当时不但是重要的精神领袖,还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政治领袖。而这个逃往政府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就同其他国家一样)所不承认的。
接待达赖喇嘛可能会被当成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举动,更会被看成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挑衅。但无论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现在的捷克共和国,或是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做出了这一行为。所以马丁 ∙ 布尔西克对索博特卡政府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斥责(4月25日《人民报》)真的很滑稽。
索博特卡政府只是奉行了前几届政府的即行政策,这里还包括了布尔西克任职过部长的那两届政府。
无论如何,哈维尔的举动还是启发了捷克乃至很多西方的政客,虽然这举动本身的原有意义已经被人曲解而变味了。
接待达赖喇嘛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惯例,无论是为了在内政上吸引某些选民,还是为了在外交上向中国施加压力。
如果这种压力带来过什么好处的话,那么这个好处肯定没有促成包容性的对话,更没有使西藏的情况好到哪里。正好相反,正因为这个原因,对话的可能性反倒减少了。因为中国对自己国土的完整产生了焦虑,这使得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不得不采取积极的防御,而这对对话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所以终止这种惯例是应该的。
达赖喇嘛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精神领袖,帮助他无数追随者战胜西方式的精神空白。但他不是国家领导人该接触的谈判伙伴。
捷中关系依然被两种简化了的设想所囚禁:一方面是努力增加收入的企业,另一方面是要求确保人权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但国家即不是企业,也不是非政府组织。
国家通过自身的外交政策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参与者创造条件。而恰恰是刚刚开始的政治关系恢复将克服深厚的文化和政治差别作为目标,并为最简单直接的相互交流和两个社会的合作创造条件。
彼得 ∙ 德鲁拉克(作者为外交部副部长)
来源:《真理报》,2014年5月2日,第十一页